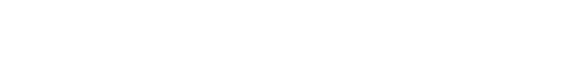编者按:校史是学校发展轨迹的记录,更是学校办学精神和人文传统的积淀,上外的传统和文脉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上外人的“坚守与创新”中得以弘扬。
校党委书记姜锋在今年的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特地向刚入校的新生们生动讲述了建校初期的几代老校友们以所学语言和知识奉献祖国,把国家责任和民族使命融入个人生命的真实感人故事。自2012年以来,校长曹德明就发起了由学生采访老校友、老教授的“文脉守望——听前辈讲上外故事”的口述项目,日前,《文脉守望——听前辈讲上外故事(第一辑)》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今年是建校65年,上外新闻网特别策划“上外的故事”专栏,专栏已先后推出《老校友陈青先生讲述赴朝语文工作队往事》、《赴朝语文工作队往事》等文章,在学校师生和校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本期刊发上海外国语大学一期校友鲍世修先生的回忆文章。
六十五年前入校生活杂忆
鲍 世 修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瞬又将迎来母校的65周年华诞。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常常爱说往事如烟。其实,生活并不完全是那样,尤其是那些当时曾让你耳目一新的情景,更是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不,前不久,读了报纸上登载的为庆祝母校65周年校庆致校友的公告后,上世纪50年代初我刚入学校时所碰到的一些新鲜事,便又不时地浮现在脑际。

我们学校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成立于1949年12月。第一批招收录取的学生,按照学校的规定,是1950年的1月5至10日入校报到注册的。当时,学校上海校区的位置不在现在所占据的东体育会路和大连路这一大片,而是在宝山路一处、曾是暨南大学二院旧址的较小园区。学校初创,白手起家,条件相对简陋,但来校的新生们,情绪却都非常高。
统一着装,这在一般学校是没有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最早的母体,是上海俄文学校;她成立于1949年12月,当时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一个分部(第4分部),所以全称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
1949年5月,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要有自已的干部队伍去接收旧政府人员,所以在当时划分的各大行政区先后成立了多所“革命大学”,采取抗大式的办学模式和实行供给制待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学,施以应国家当务之急、为建设需要而学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自愿无私奉献、崇尚埋头实干的好干部。。
上海俄文学校,作为当时革命大学的附设学府区别于国家教育部门管辖下的一般高等院校的第第一个特点是,对招收进来的学生实行供给制,即不仅不收学生任何费用,而且给学生免费提供膳宿和服装。
服装是统一制式的,颜色为灰色,这不是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北所穿的衣服一模一样嘛!
记得,在领取有生以来第一套这样的制服时,心情很不平静;穿上了以后,更是非常自豪,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已把一生交给了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成了自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名革命者。
日常教学,实行小班化制度
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行连队化管理,是上海俄文学校区别于一般高校的第二大特点。
那时,我们每个新生报到注册后,首先会被编入一个小班,小班的人数在25到30人之间;待12个小班的人员满额后,则成立一个大班。每个小班,设有由学生担任的正、副班长;而每个大班,则由学校派干部来充当班主任。
小班和大班各有自身的功能。

按“革命大学”的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入学后,先要接受3-4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接受思想改造”。在这一时期,学生们常要聚集到一起,去礼堂听各种题目的大课,如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等等,不一而足。而这时,就需要按大班成队地带过去。另外,当时,校园的环境卫生,都是由学生自己定期打扫的,这又需要按各大班来分片包干。再就是,如果学生要出校参加市里的某项集体活动,那也是得按大班编队循序前往。
小班,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专业教学两个方面,作用都非常巨大。“接受思想改造”阶段,同学之间的互学互帮,都是在小班进行。这里有大量的对话攀谈,要掏心窝子,范围越小,越便于启齿。而在语言专业教学方面,则更是不能没有小班。首先,实行小班教学,老师能关心、照顾到每个学生;同学之间也便于交流互学。
为加强对学生课外活动的管理和关照,当时,学校规定有离校返家或外出留宿的各项请假销假制度,而负责监督执行这些制度的,正是各小班的领导。
师生、同学间,关系亲如家人
这是上海俄文学校,在办学上,区别于其他高校的又一特色。
学校在开办之初,就明确宣布,同学之间,一律以“同志”相称;师生之间则应待若家人,做到形影不离。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当时的确也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认真。这实在让生活于其中的这批莘莘学子,即建校之初收录的这第一批学生,受益不浅啊!。
在进上海俄文学校之前,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夏中学和同济大学,回想那两个学校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处相伴,一般都比较客气并保持有一定距离。在当时的校园里,同学间,见年长者称兄,年幼者道弟;而老师在学生眼里,则是尊敬的长者,除在课堂认真听讲和提一些实在难懂的问题外,课下是很少再去打搅他们的。

解放以后,学校师生、同学间相处的氛围显然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在上海俄文学校,则更是不一样。同学间,由于经过了“思想改造”学习,相互间对彼此过去的经历和个人的志趣、今后的意愿,都有了深刻了解,所以,叫起“同志”来,自然十分亲切,同时也表达出了情同知己这层不同于一般的诚挚关系。
说到师生之间要做到待若家人,形影不离,这除了显示出对彼此感情上亲密融合的一层要求外,从语言学习收效的角度看,师生间,没有课上课下高强度的跟踪教学连轴转、那是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语言教学的明显成效的。我,可以说是这方面,最明显的受益者:1950年1月入校,先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改造”学习,还跟大家一起休了一个月暑假,可到了当年11月上旬,我就奉派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受领一项独当一面的俄汉、汉俄口笔译双重军事辅助教学任务,并在那里一干就是10年。请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当时我那位辛勤忘我的老师,在课上课外全天候对我的精心培育和我自己所做的、持续的刻苦努力,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把“伙食尾子”,用来“打牙祭”
因为是供给制,学生的早、中、晚三餐,都是由学校统筹的。建校初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办学的经费有限,我校当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低,平常较少能吃到荤菜。学校管食堂的干部,常为如何改善学生们的伙食质量,费尽脑汁。
这些在学校管后勤保障的干部,大多是从解放军转业过来的,他们带来了不少在部队为士兵办伙食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每个月都要用好“伙食尾子”。
究竟什么是“伙食尾子”呢?所谓“伙食尾子”,指的是:学校每月拨给用于学生的菜金是定量的。如果管食堂的干部能精打细算、在快到月底前,还能多少结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伙食尾子”。
有了“伙食尾子”,大家都会乐于尽情地享用,好好吃一顿丰盛的荤餐。这叫“打牙祭”。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点让人激动。最早在暨南大学二院旧址时。学校根本没有专门的食堂。学生们用餐,就在一处没有桌椅的空教室,站着对付。但一到“打牙祭”的时刻,学生们仍都会欢快地聚到一起,每8个人,围着一个盛满红烧肉煨白菜的大洋铁皮菜钵,兴高采烈地饱餐一顿。
最后,在母校65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还是要向上外,这位在我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和后来在军队从事国防科研事业不断前进过程中的逐步成长,都曾施加过重大影响,即曾事先在思想品德、语言专业知识和就业基本能力等方面做过厚实牢固铺垫的、热心的母亲,道一声深深的感谢,并预祝母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鲍世修:上海外国语大学一期校友,通英、俄、德语。1950年大学毕业后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在军事科研机构从事外语译校、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任译员、译审、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等职。1990年后,转而参与地方科研、媒体和学校等单位的专家咨询工作,先后应邀去德国、法国、芬兰、瑞典、挪威、俄罗斯和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