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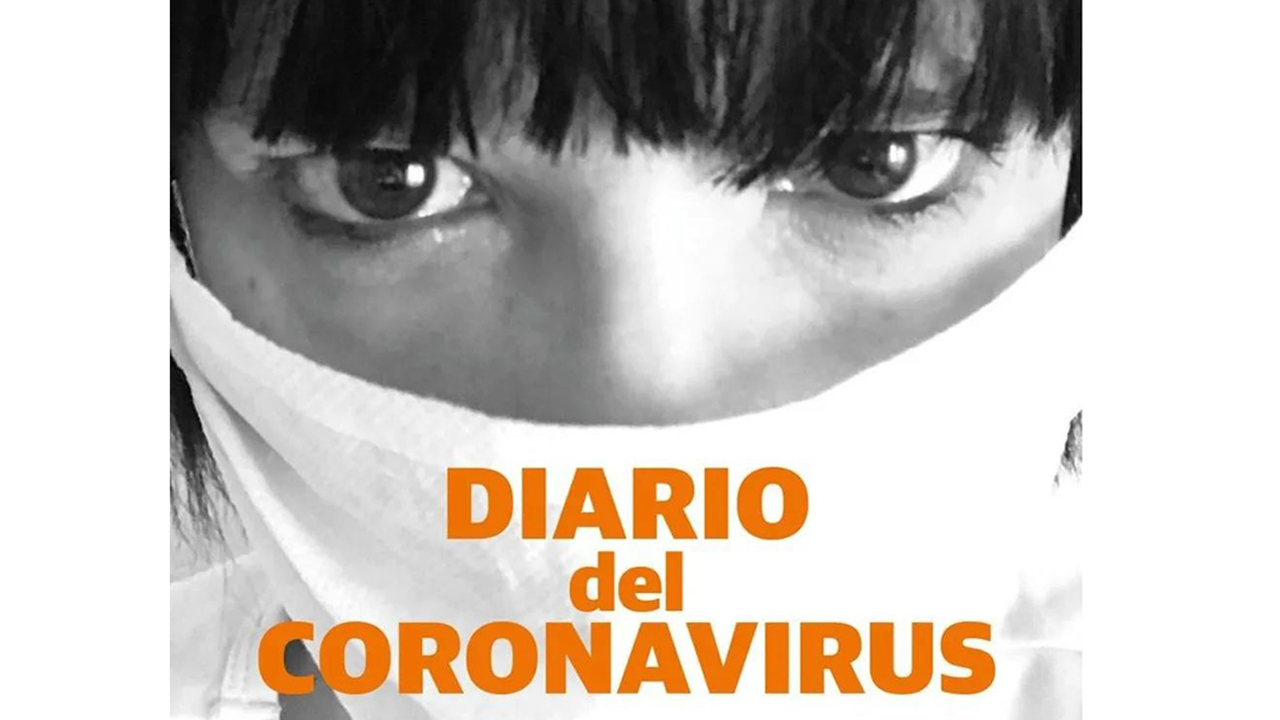
原文《异军突起的新冠文学》,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张帆教授、博士生牛金格。 【摄影 | 】
-

【摄影 | 】
-

【摄影 | 】
-

【摄影 | 】
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正对文学提出全新挑战。瞬息万变的疫情正颠覆读者对文学的期待,并给叙事带来结构性难题,文学该如何介入灾难现场,文学何为?
2020年4月1日,作家弗洛里安·维尔纳在德意志广播电台官网发表《新体裁:新冠文学——阅读有感染力》,率先提出“新冠文学”,吁请作家直面写作新命题:在新冠疫情下如何与生活相处,助力人们在灾难降临时寻找生命意义,重识身份归属。
非虚构:“急就章”实录疫情时代
新冠疫情爆发伊始,“封城”“隔离”使个人化非虚构写作走俏。奥地利格拉茨文学馆呼吁:“我们需要借助文学的反思力量,理解当前措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巴赫曼文学奖得主比尔吉特·比恩巴赫就在日记中分享了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片段。奥地利首都出版社官网开辟专栏“新冠博客”——“紧急状态纪实”。四十位作家踊跃参与,从维也纳到阿布贾,从莱比锡到伦敦,从格拉茨到斯特拉斯霍夫,“新冠博客”成为交流互动平台。奥地利文学荣誉奖得主芭芭拉·弗里施穆特在《无尽的新冠病毒》中写道:“我早上打开平板电脑,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新冠疫情的内容;中午听新闻,除了新冠,几乎没有别的消息;晚上打开电视,还是新冠。逃离新冠是不可能的。”
除文学馆、出版社等机构组织的集体写作外,众多作家自发创作。德国作家大卫·瓦格纳的日记《围着房子转》发表在德国在线“时代周刊”,坦然曝光新冠疫情下生活的“瘫痪”。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生活被强制按下了暂停键。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得主保罗·乔尔达诺的日记《新冠时代的我们》记录了面对新冠疫情的心路历程,一经出版就被译为几十种语言,然而,如果读者期待从阅读中获取任何关于欧洲疫情的宏观叙事,恐怕会大失所望。
围绕新冠疫情,作家们还创作叙事散文、实录故事等。德国作家阿诺·韦德曼出版散文集《新冠疫情的早期场景》,记录人们对当前形势五花八门的判断和看法。奥地利前政治家马蒂亚斯·斯特罗尔茨以新冠疫情为主题撰写短篇故事集《这个时代的力量和灵感》,通过17篇故事讲述感人肺腑的真实事迹,分享应对疫情和危机的有效方法。奥地利作家索尼娅·施福出版文集《新冠——一切将与以往不同》,实录社会各阶层在疫情中的故事,传递和谐、团结的积极理念以及“化危机为机遇”的乐观态度。
虚构与想象:赋予作家更多创作空间
相较非虚构的纪实性写作,抒情言志的新冠诗歌有感而发、凝练精悍,是作家寻求慰藉的主要文学体裁。苏格兰女诗人卡罗尔·安·达菲创作诗歌《手》,以此发起“写下我们的现状”活动,召集世界各地的诗人用诗句记录蔓延的疫情。《纽约时报》在《致编者的新冠诗:“死亡也戴口罩”》中刊登11位读者创作的新冠诗歌,其中由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纳瓦拉·斯科特·莫马戴创作的诗歌《疫情时代》,描写了大众的惶恐和疫情对人际关系的逼仄。
美国文学杂志《拨浪鼓》的专栏“诗人回应”,发表新冠诗歌多达几十首。英国“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在《卫报》发表诗歌《封城》,揭示了疫情虽使社会放慢步伐,却也让人们变得更加明智。他联想到,几百年前不幸感染鼠疫的亚姆人面临同样的困境:村民把钱币放进界碑的洞眼,以购买外界的物资,并在洞里倒满醋酒清洗钱币。几百年前,物资匮乏且医疗落后的亚姆人尚能直面饥饿、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主动进行封锁隔离,这一英勇而明智的壮举,不仅向我们传递面对疫情的勇气,也传授给我们应对疫情的经验。
随着疫情逶迤纠缠,虚实结合的新冠小说赋予作家们更多的施展空间。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格拉文尼奇在德国《世界报》官网连载《新冠小说》,揭示了在疫情失控与经济走势下行的双重夹击下,疫情对社会造成难以弥合的创痛。奥地利女作家玛蕾娜·施特鲁维茨亦在个人网站连载自传小说《世界的现状》,以第三人称叙述了总理库尔茨下令封城、生活停摆的情形,揭示“紧急状态”对社会、艺术和生活的影响。苏格兰作家艾莉·史密斯以新冠肆虐取代脱欧成为英国最紧迫的难题为背景,创作新冠小说《夏》,围绕主人公萨沙和罗伯特内心世界的刻画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讨论交相呼应,展示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对自身世界观的重塑。
尽管,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生活,但人们不会坐以待毙,而文学此时能够做到的也许就是真诚地直面疫情,不惮前驱,减少人们对新冠的疑虑和恐惧。德国女作家罗拉·兰德出版《创世之冠》,描写疫情使主人公的乡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是谋划过好每一天。
直面新冠:文学承载的意义
肆虐全球的疫情引发人们思考文学在历史重大事件中应当肩负的责任及承载的意义。新冠文学作为一种应景的文学体裁,也遭到诸多批评与质疑。德国作家兼记者扬·德雷斯在推特上呼吁不要创作新冠小说,因为人们对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疫情知之甚少,任何有关新冠疫情的文学作品都会被视为挑衅。但德国作家玛里昂·帕尼松亦为新冠文学辩护:“疫情期间创作的诗歌并非幼稚,相反,许多迹象表明,人们在隔离期间创作的诗歌视角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然,这也是诗人应对危机的一种策略。……疫情期间的诗歌创作绝非任意而为,毫无反思。相反,诗歌在新冠危机中产生了一种抗体,以对抗封锁、孤独、压抑、焦虑等负面影响。”法国作家奥蕾莉·帕罗德称赞新冠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疫情之所以产生文学魅力,是因为它对我们共同生活的能力提出质疑,并且揭示了社会结构及其得以持续运转的重要性。”
对于新冠文学承载的意义,人们也给出不同的解读。德国评论家安妮·多尔·克罗恩认为:“虽然新冠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否经久不衰,尚未可知。但如果未来某一天,有人想知道当年一个小小的病毒怎样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他便可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形。”玛丽·施密特则认为,新冠文学的价值可能要等到疫情结束才能显现。
如今新冠文学由最初的零星散布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正如德国《每日镜报》评价瑞士作家马丁·迈耶的新作《新冠》时断言:该作“大抵是卷帙浩繁的新冠文学作品的前奏”。新冠促使作家与读者的习惯发生转变,他们将作品刊发在个人网站与媒体官网,促进了网络文学的繁荣和传播速度。新冠疫情虽尚未结束,但新冠文学承载的意义逐渐凸显:第一时间记录疫情中社会状况与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成为人们反思的媒介,抚慰疫情当下迷茫无措的大众,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它的爆发与迅速蔓延印证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事实,各国作家通过新冠文学应对疫情则强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