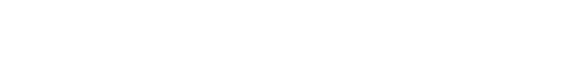编者按:《环球时报》2014年2月14日第13版(文化教育)刊载了我校党委书记姜锋的署名文章《近距离对话翻译界泰斗》,本网略作修改并转发,以飨读者。
1984年秋,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工作,年底进驻北大参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组,配合做外语文学科研规划工作,为此得以有机会拜访季羡林、冯至、朱光潜、罗大冈诸前辈,求询其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应如何规划等意见,其间所闻,至今难忘。
访季羡林先生是在他北大的办公室。季先生身穿蓝色中山装,整齐地扣着领口,胸前可见一些饭渍余迹,坐在四周满柜图书的房间中央。谈到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态度,老人说,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点和结果,这样研究才能丰富活跃。他提到在全国人大的一次经历:当时人大刚装电子表决设备。一次表决时,显示器上显示有人按了反对票,他身边一位老大姐惊讶地说:表决器出问题了,怎么会有反对票?季老讲完这个经历沉默片刻,之后也没评说。但他的意思十分明了。
朱光潜老人当时走路已显困难,校园内偶遇,崇敬之至。他的《谈美书简》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外德语系同学中几乎人手一册,启蒙着人们认识美学。老先生听说我是规划组的工作人员后,竟自我批评起来,说自己对马列研究还不够,尤其需要学好外语,以便全面领会马列原著真义。他提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认为“终结”的德文是Ausgang,是“出路”之意,译成“终结”是错的。先生的严谨让我十分感概。
拜访罗大冈正值他获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不久,他的著作《论罗曼·罗兰》再版。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979年,当时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今非昔比。罗先生表示,书出后称赞和批评都有,甚至指责,但他不想急于反应。研究者关键是认真收集、整理材料,这是真功夫,不能马虎,至于结论则见仁见智。
拜访冯至先生是在他建国门外永安里家中,房间四周书架整齐地摆满书籍。冯先生当时已患眼疾,他在访谈的某一刻望向窗外,茫然深远的眼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感叹:研究文学要关心科技发展,有人要用基因把动物转变成人,那以后该怎么定义“人”呢?!一位大文学家,深切地关心着科技变化,思考着其对人类的影响,这在当时超乎我的想象。
季先生的宽容,朱先生的执着,罗先生的坚守,冯先生的人文视野与关怀,感念与几位先辈一生仅有的一次相遇。此后再无相识的机会,但其精神却如镜在前,经年不忘。精神是点滴实践的沉淀和积累,不是呐喊和规划的成品。评说先辈精神时,我们已把自己放在旁观的位置上,但被旁观一定不是先辈所需要的。他们期待的是同路人。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