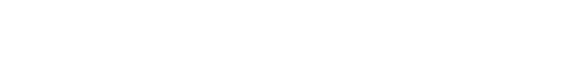我觉得我该写点东西了。
这么久了,是该写点了。
这几天一直在疯狂地看关于许知远的东西,书,专栏,图片,我甚至还在网上搜了“许知远 妻子”关键词。我想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知道关于他的更多所有,尤其是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写到过的大学日子。再转身回头看自己的日子,一半是跟着学霸走,一半是跟着放纵的自由,也会像学霸那样坐在桌旁很认真的做高数,完
前天晚上躺在床上看着《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凌晨一点多,身边没有活人的气息,我一直想在这本书中搜索着任何一些关于青春印记的只言片语,只是,当我回头时,我才发现,这本书的每个标点都沾有青春酸涩的味道。
在高中时,在某本杂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许知远,那上面他的图片至今刻在我的脑海,只是从被记忆到被回忆相隔了好几年,我看见他带着令我羡慕的慵懒姿态,双手搁在椅子上,但关于他脸上的表情,我却忘记了,似乎是嘴角挂着极浅的微笑,但在看了他与许多人的对话后,我就不敢再用“极浅的微笑了”,而是会用“任何刀具都刮不动的脸”。看了无数的人物图片,为什么却对一本杂志上的一位作者如此记忆深刻,他长得不帅,“长满粉刺的脸上显示出一幅苍白无辜,眼睛迷离地斜望着一个地方,除了飘逸的长发他一动不动在那里沉思”, “长了一副狼模样,夹着灰白泛黄颜色的一头卷毛,痴痴地看着访客,似乎还流着口水”。
我想必然无疑是那篇文章让我触电了,他的精英创造历史的观点。当年的我,是个整天拿着政治书背的呆子,除了发呆,偶尔想想女孩,吃喝拉撒之外,就是背书,老师耳提面命地教育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啊”,渴望在大人搀扶下行走的我摇头背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啊”。第一眼看到这篇文章,我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赞同他的观点,我可能在想——哗众取宠的家伙。
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家伙,我只是意识到,我喜欢他的笔风,喜欢他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令人不知所措的文字,我看到一段评论,“那种优雅而深沉的文字,在那种故作迷离的文字中,虽然不能得到一种确定的观点,但是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还有比这更迷人的么?”当时我大脑一震,没有蛋疼,也没有菊紧,只是内心一抽的瞬间,我仿佛走在一道漆黑的地洞下,只能往前走,木偶般察觉不到任何东西的感觉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文字,却是让我看见了光,看见一双擎执有力的双手在向我召唤。那时候,我突然感觉,找到自己所钟意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在你看见它的小于一秒之内的时间里,你的心里有一种感觉很温暖,随意,妙不可言的东西在窜。过了一秒之后,也许我们的世俗,我们被禁锢的思维就会像一团炽热的火焰般将你的温暖焚烧至尽,所以你得捕捉最原始的感觉。
昏黄的街头,几把伞,路灯照得地面支离破碎,散发着酒味的嘴,在肆无忌惮地吼,对面阳台有人骂。跟这种生活很像的就是曾经许知远在青春迷茫时对于现实的不安,他的文字本身带着力量,给人一种生之为人的存在被得到证明的快感。谁的青春不迷茫,也许他到现在也还是迷茫,我们一起迷茫,在这茫茫的大雾中,有人匍匐,恭恭敬敬地用手摸路;有人闭着双眼狂奔,摔下悬崖,粉身碎骨;有人站着不动,在可见度内看岁月剥离,风化青春。
无数群飘飘荡荡的魂灵啊,你们在为何恸哭,是在哭泣曾经逝去的那再也填不进的青春格子么。你可知道我们在青春的大雾中行走青春,那拖鞋的回音里藏着的是我们深深的恐惧啊。一代一代,我们跟任何一代都一样,前赴后继的年轻,然后在某个寒意渐浓的下午,夕阳染红的房子里,像邂逅猛兽般,看见一条条的皱纹,在蔓延。害怕衰老,是害怕自己的存在被上帝之手抹去,这害怕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因子,这因子束缚着那凸起的青筋所包裹的心。
不去虚伪地充当一个乐观者,不在孤独迷茫时掩饰我的落寞。
当地狱之火,席卷过所有在哭泣的魂灵时,我也为你们而哭,为你们那向往的回不去的好时光,为你们那永远飘在空中的青春。
(国教学院 张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