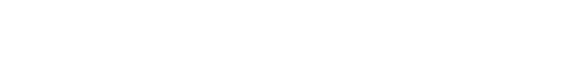杨小石教授简介
杨小石,男,北京市人,1923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
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获学士学位,先后在上海私立华侨中学、上海私立中正中学、上海光华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1956年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英语教研组工作,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1980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至1991年间,先后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州大学和衣阿华州瓦特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3年退休。
曾参与编写《英语》教材第七、第八册。翻译(英译汉)《王孙梦》、《干旱的九月》、《他的寡妇的丈夫》。翻译(汉译英)电影《舞台姐妹》、哪吒闹海》、《小花》、《沙鸥》、《孔雀公主》、《梅花巾》、《候补队员》、《特区姑娘》、《大庆战歌》《毛孩》、《大足石刻》、《崂山道士》、《大漠紫禁令》、《人鬼情》。为多部英语有声学习资料录音。参与多部电影配音。
采访人:
杨小石教授:也说不上。因为我爸爸早年到法国、瑞士留学,妈妈是瑞士人,家里常常用法语。我小时候在北京上的是法国人办的法语小学,读的都是法国小学生的课本。毕业后,我父亲觉得我中文不好,中学就让我到北京的一个教会学校,叫育英,在北京我们这个中学可以算是第一块牌子,是最好的中学。当时有两个教会学校成绩最好、最突出:一个是育英,一个汇文。在育英,我是个奇怪的学生,上国语课我退了三级还是跟不上,但是我的英语是跳级上初一的,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中学毕业。
采访人:您当时大学里都开什么课程?您所有课程都是在重庆读的吗?
杨小石教授:不是。我最后一年是在上海读的。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复旦迁回来时,我就回来了。我开始念政治系。那时候我觉得我英语不发愁了,就不念英语了,念个不同的。一年级的学生上文科、理科都是共同的修,课程比如说哲学、历史、三民主义,逻辑学,选课算学分。但政治系念得实在没味道了,就转到外文系去了。共念了一年政治系。我们那时候念书有大一英语、大二英语,三年级、四年级就读英诗,英国散文,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美国二十世纪文学等,有些课是必修的,有些课你选了算学分。那时候抗日战争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在嘉陵江边上,房子都是用竹子搭的,表面糊些烂泥,上面弄个顶,弄些瓦,墙跟屋顶还有空隙,冬天就呼呼漏风。墙壁上也就刷些白泥巴。洗脸水是从嘉陵江挑的江水。一人发一块明矾,泥沉下去了,才可以洗脸。而且臭虫成灾,学校每个月都会把床放进大铁锅里面煮一下,可还是不管用。图书馆里有几个大煤油灯,比自己宿舍的灯亮很多,每天晚上大家就站那排队等开门,六点图书馆一开门,大家就拥进去占位置。
采访人: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呢?哪些老师是您最喜欢的?
杨小石教授:我做学生的时候有很多好老师。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特别严格,他给我们上的课是非常好的,(他)叫全增嘏,教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程。林同济是教散文的,也教西洋政治史。我喜欢上戏剧。戏剧老师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名人,戏剧家洪深老师。他只是上课,没教我们表演。我们上课看剧本、写报告。他就跟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个副校长一样,叫你分析一个角色,或者是对故事进行分析,或者对主题思想进行分析。
我在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老师姓徐,徐宗伯,是个福建人。他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呢?是复旦大学上个世纪初的第一批毕业生。肥头大耳,穿长衫大褂,剃光头,完全不像教英语的样子,像说相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我从他这得益很深,他特别严格,写篇作文拿回来改得都成大花脸;人也挺怪,纯粹书呆子式的人物,手不离卷。那时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复旦在重庆的远郊区,放假了,我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看着
他的笑话还挺多的。重庆夏天非常热,他就在马路边上找个小的河沟把毛巾弄湿了,搭在光头上,穿着长衫,拿着一把大芭蕉扇,穿双布鞋,像济公似的。结果有一天
采访人: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杨小石教授:我从复旦毕业后通货膨胀很厉害,为了糊口,单做一个职务不够,我有三个职务,一个是在国防医学院教公共英语,还有一个是光华大学英语系(后来并入华东师范)当助教,也是教学生外语;然后在一个中学里面教两个高三班。中学里面待遇好,发东西,发食物,如米、油,受通货膨胀影响小一些。
我后来在报上看到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日报登的广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愿意来参加革命工作的欢迎来报名,我就去报名了,之后就到二军大,那时候是第三野战军人民医学院。54年,55年,二军大取消,英语课都停开,不要开设帝国主义语言,要一边倒学俄语。54、55年一般的学校那时候都不学英语了,只有复旦还学。二军大的人事处就找我谈,给出几个选择:一个是去复旦,一个是去社科院,一个是去外语学院。那时候我在俄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夏仲翼教授,他说外语学院的西语系是新开的,很有盼头,有前途,有奋斗目标,咱们一块去外语学院吧,复旦不少我一个。那么我就这么来了,来的时候刚好是要从俄专转到外国语学院,那时人事处的是周一光,校长是涂峰,他们叫我来参加筹备工作。那时西语系含英德法三种语言。西语系最早的系主任是方重,分管三个教研室,英语教研室,俄语教研室,德语教研室。那时英语教研室我是头,法语教研室是董寿山,德语是李晓。当时做筹备工作的时候我负责面谈录用社会上的教师。经过我手上有一百多个教师,法语我也进行面谈的,德语我不会,所以英语法语我都管。那时人事处、校长也说差不多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可能的教师我们都吸收进来,之后的事进来再说。
采访人:
杨小石教授:我上四年级翻译课。那时候我们外语学院是比较领先的,61、62年,给学生不是一本书,是上一课给一课,后来订在一起,一本教材故意拆开,不让提前看,老师挺严格的。当时是费了很大力气编了这教材,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任课的每个老师,国家教委下面的领导,组成一个教研组在里面编,叫《英语》这个教材。我们编了许多教材,有统编的,还有四年级的7、8册。那时候有一套是用的许国璋的一、二年级四册,5、6册是南大,7、8是我们编的,我们和复旦。
采访人:是什么促使您走翻译方向?
杨小石教授:其实我本来爱好写小说,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作家写小说,用英语写,面对国外的读者。因为解放前后这段时间外国记者都没有了,中外有很大隔阂,外国不了解中国,那时候苏联叫“铁幕”,外国都不了解解放后的中国。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说法说是苏联是“铁幕”,中国是“竹幕”。我的理想就是介绍新中国的情况,用英语来写小说。那时我真是下了功夫,解放前后差不多有四年多的时间就是早上抹黑起来写到晚上半夜,一天就睡四个多钟头。用英语写了差不多四百多页小说。那时候没地方发表,这个稿子就一直搁在那儿,搁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心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都烧掉。
那时写小说很危险,要表达自己的言论还要反复斟酌,所以没法写小说就转到翻译方向去了。我没留过学,没出过国,就是低着头写写写。创作不能发表我就发表译稿。给《中国文学》翻了许多东西。我主要是搞中翻英。英翻中也搞,是次要。
科技、教育、美术,故事片,长篇短篇各种文体的都有。那时是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时候,最早翻的是《聂耳》,后来搞了一个比较重磅的东西就是《舞台姐妹》,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片子。《舞台姐妹》后来拿到中美飞机航线在飞机上播放的。我们搞了很多,还有《沙鸥》,关于打排球的。当时也把中国电影的剧本翻译成英文,然后配音。这件事很难的。我镜子现在还摆在书桌前呢。念中文剧本,按中文翻英文然后看(镜子里)口型还对的上吧。我刚开始搞电影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闪闪的红星》里我给老头配音,导演说我笑得不像,我就从译制片厂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反复练习那个笑,路上总被人当精神病。后来导演说我笑得很成功了。
最近我翻译了几部昆曲,完全押韵,但是数量不多。都是押韵的,一行对一行,这个难度非常大。我作动画片也有两三部是押韵的。我现在觉得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当局不是很重视译制文学作品出口,特别是电影、电视剧,我觉得这些也是大有可为,但这个行当好像是死掉了。现在像张艺谋有些大片呢它们也到国外去放,但他们字幕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给做的了。我现在对于这些很不乐观。现在除了是上海台、北京台报新闻的这些英语是过关的,平常的各个台一出英语就错。
采访人:
杨小石教授:薄弱环节是中翻英,还有就是完全用英语写。另外我觉得学校老师应以教学为主,但不能否定科研。我们的外语工作者看多少书我心里没数,我做学生时条件差,图书馆书不是很多,整个图书馆的英文书我都借出来过,阅读量相当大。一本长篇小说看三四天,记得《外交家》就一本,大家抢着看。我一拿到手,就熬夜看。有时会记记,多数的书都是很快看完,特别好的书有时会再看一遍。不管怎么说阅读量要很大。现在学英语,有几本书非看不可,跟西方文化挂钩的,《圣经》一定要看,新约、旧约都看,因为许多典故就是这里出来的;《天方夜谭》,《伊索寓言》必须要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一定要看,这是知识的问题不是语言的问题,非常多典故都是出自莎士比亚,就像中国典故许多出自三国,什么“英雄所见略同”都是三国出来的;希腊罗马神话也要通读。没有这些就是缺少文化。
现在除了上课,还有科研。搞外语工作,与社会怎么挂钩?怎么做贡献?我们的方重先生就做得挺好。杨宪益、王佐良这些人也做得很好。要把外面好的东西介绍进来,还要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看来,介绍出去比较难,要好好做这方面的工作。
采访人: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情况,谈了这么多您的经历。祝您健康幸福。
采访人:徐文文、蓝茹
整理:蓝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