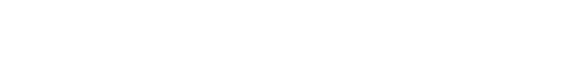回忆为上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奋斗的那些岁月
口述:韩宗琦
时间:2008年10月7日
采访、整理:缪迅
采访前记
韩宗琦,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入党。先后任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宣传队分队长、连指导员,山东省滨北胶高县海青区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边区工商局干部科科长,江苏省苏南行政工商局秘书、党支部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华东区油脂公司上海粮油进出口公司人事室主任、副经理,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公私合营上海市进出口总管理处总经理,上海市外贸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上海外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1, 上外与外贸学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是1972年随着上海外贸学院并入上外而来上外工作的。“文革”结束后,担任党委领导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有幸与广大师生员工一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参与了平反冤假错案这一事关上外几百个人政治生命的工作,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为此感到欣慰。
我是一名老党员,1938年我14岁,小学刚毕业就参加革命了,1940年入党,那可是战争时期啊,十多年不知打过多少大小战斗,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以后,我来到外贸部门工作。
我是1972年那年随着上外与外贸学院的合并而来到上外工作的。1972年,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为什么外贸学院要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合并呢?这里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外贸学院的成立和办学事业离不开外语学院。这两所大学在办学历史上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了。
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外贸部就已经在考虑:怎样来培养青年外贸人才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做贸易的人才,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呵。由于过去是“一统天下”,一边倒,即只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做贸易,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大来往的。像英国、法国等一些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大和他们来往,和美国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时,我们国家已经建设了10多年了,和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使两国关系也差不多濒于决裂。在这种相当“孤立”的情况下,我们自己要考虑怎样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这就迫切需要培养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的人才。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决定,由上海这个大口岸来带头做这方面的工作。从历史上来说,上海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很多。培养自己的外贸人才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外贸人才是有点历史渊源和人才基础的。所以,经上海市委和外贸部党组研究,确定首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成立一个外贸系,以后改为对外经贸系。到了60年代中期,就在上外这个经贸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上海外贸学院。
上海外贸学院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64年、65年,在上海外语学院外贸系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1963年,我经外贸部批准到欧洲考察。那时对外叫考察团,对内叫考察组,由我担任组(团)长。主要任务是去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的情况,研究如何把我国商品打入欧洲市场。同时推销我国大米、蛋品、油料等农副产品,换取小麦等便宜的欧洲国家货物,以缓和当时国内的物资供应紧缺(那时的一吨我国的大米可换取三吨半左右的小麦),并就打开与欧洲国家的外贸局面提出相关建议。我去了两年,在欧洲一共走了7、8个国家。那时候,我国和英国刚刚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和法国、意大利等都没有外交关系。1964年7月,我们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的十来年中,又陆续和瑞士、荷兰、意大利、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逐步地在欧洲打开了外交与外贸工作的局面。
1965年上半年我从欧洲回来以后,上级为了进一步培养外贸人才,把我从市外贸局副局长的岗位调到外贸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由上海市外贸局齐维礼局长兼。我作为副局长还兼了外贸学院副院长一职。谭守贵同志任党委书记,谭守贵同志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那时候他的身体就不大好。(上海外贸学院当时直属中央外贸部领导)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天下大乱,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由于我前两年在国外,回来以后,在市外贸系统开的几次大会上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情况,并写了许多书面报告和资料。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我作为上海外贸学院与全市外贸系统的走资派而且是外贸学院的头号走资派“揪”了出来。
虽然被打倒、被批斗,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我觉得我没有做过任何违反党的宗旨的事,我忠于党,从小就在党培养下,在艰苦战斗中成长。所以我心里清楚,我既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至于所谓走资派嘛,那个时候,走资派非常多呵,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开始,还有那些老帅等很多很多的老干部都成了走资派,所以弄一顶“走资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也不怕。心里比较安然。虽然造反派天天批斗我,对我实行隔离、劳动、大小会批判,戴高帽、游街、下跪等等,受尽了许多折磨和人格侮辱,但是我心里比较平静。我觉得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
1972年,中央派外贸部老部长李强和副部长傅生麟到上海来,李强和傅生麟就外贸学院是不是还要办下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就看中央了。根据我的看法,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办下去。那时候要把外贸学院恢复确实是很困难的。过了没多久,大概是1971年秋,教育部刘西尧部长来上海,住在淮海中路东湖路上的东湖宾馆,他专门为此事把我单独叫去,我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的调查报告》上所做的批示即著名的“7.21指示”。大概的意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工人农民当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7.21指示”对文科类院校要不要办却没有提及。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外贸学院和外语学院合并办学。目的是为了使外贸工作者能熟练地掌握外语。1972年,外贸部傅生麟副部长又来到上海,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个别找我谈两校合并的事,连秘书也不在身边。看来基本上是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记得,当时的合并先从两校的“五七干校”合并开始。那时候,基本上两校的人都搬到安徽凤阳大庙的那个干校去了。外贸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干部、教师都在干校一块劳动,编成了一个队伍,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合并”。两校合并的过程大体就是这样的。
2.十年动乱,上外遭受巨大的劫难
1972年外贸学院和上外合并那时候,两校干部和教师的思想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看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人心惶惶、极度地悲观,对前途不知所措,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文革中有些干部、教师家破人亡,家人互相不能见面,整个学校也可以说是破乱不堪。为什么?因为很多干部和教师都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等,大部分教师和干部都成了“九类人”。所谓“九类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臭老九”,而所谓的“臭老九”(指所谓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为什么叫作“臭老九”,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所谓的“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不受信任。
上外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很“出名”的,学生的“造反精神”相当激烈甚至很残暴。对干部、教师的批斗和人身摧残惨不忍睹,相当的严重。可以举两个例子:文革初期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李家齐同志后来告诉我,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市委王一平书记,说上外批斗干部、教师相当厉害,请你们赶快来人。于是王一平书记派李家齐来上外看看情况,他一看那情景,真是太惨了:只见上外的大批干部、教师被集中在大操场上,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残酷批斗,头上戴高帽,脸上被浇上黑墨水,被用皮带抽打,被逼着在操场上下跪、爬行,有的甚至被逼着从操场爬着出校门,一直爬到离上外校园有数百米之远、位于中山北一路上的上外附中校园里。
文化大革命前期,其他高校的造反派们都到上外来“取经”,即来讨教怎样迫害干部教师的“经”。当时的上海市委还没有完全靠边,对上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市委认为,上外在上海各高校中是造反造得最厉害的,对教师、干部的批斗也是最严重的。
第二个情况,当时外贸学院的学生和外语学院的学生彼此都有联系。文革期间,两校的红卫兵组织互相之间串联交流,外贸学院的造反派把上外造反派怎样批斗干部、教师的做法都搬到了外贸学院。所以,外贸学院成了外语学院的一个“翻版”,上外怎么斗人,他们就怎么斗。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上外在文革中是“重灾区”,遭受破坏的情况极端严重、惨烈,文革“后遗症”也非常严重,积重难返。所以,当时的上外人对前途是极端地悲观,人与人之间不敢讲话,互相猜忌。
那时我一到上外,映入眼前的上外情景是:不到100亩土地的校园破乱不堪。当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所以每个单位都在挖防空洞,校园里挖得一塌糊涂,到处是破砖破瓦,还有就是大字报满天飞。学生无心学习,男女生混杂,男女宿舍都不分,没有什么纪律,没有什么秩序,不讲卫生、脏乱差比比皆是,让人不堪入目。
当时上外领导的权力集中在工宣队里。以后又派来了军宣队,党不管党,党组织都停止活动了。党员甚至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了,更不必说自己是“先锋队的一员”了。工宣队当领导,大家心里都不服气,但又不敢讲,只能低声下气的。
那么工宣队和军宣队是什么关系呢?工宣队中有的是老工人。一般的老工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有些人造反精神是很厉害的,他们内部互相间出现不团结的现象。争权夺利,相互之间吵架,工宣队与军宣队人员乱搞男女关系的也有,根本形不成什么“领导”。这就是我1972年来上外时看到的情况。当时,我和上外的干部、党员、全校教师一样,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从上外一个学校的“缩影
就可看出当时整个国家的情况。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4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不久邓小平同志顶着重重压力,提出“要整顿”。于是高校迎来了文革期间的一次“整顿”。上外从1972年恢复招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7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上面提出,上外要重新建立党组织,所谓以“老中青三结合”成立校党委。由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干部组成党委班子。党委班子由上级任命,也不开党代会选举。上外党委班子组成后,任命我为党委书记,而实际上学校的大权还是在工宣队、军宣队手里。开会时就我一个老干部,孤家寡人一个。各系各部门的班子也都有工宣队、军宣队参加。总之,还是工宣队、军宣队当家。名义上有党委,实际上并不是党委领导,名不副实,党的领导被严重削弱。
当时上外的情况在建立党委以后,就是这个状态。教师根本没有在教学中起到什么主导作用。学校实际上也不是以学为主,还是以所谓“斗批改”为主。大部分教师干部下放到凤阳干校劳动,一年里有半年时间是在农村劳动。可以说,那时候的干校实际上是“劳动集中的地点”、“劳动改造的地方”。看干部或教师的表现不看别的,就看你“劳动表现”如何。
1974年,上外曾发生震动全校的大事,即所谓“党委书记反工宣队”,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颇为罕见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起因是有人打报告给市总工会,这个报告谁写的一直没查明。(我估计可能是工宣队内部的人)这个报告送到了市革委会、市总工会。当时的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都作了批示,并派出工作组进驻上外,在上外开大会宣读马徐王的批示,称上外党委反工宣队。工作组在上外连续召开了70多天的大小会议,揭发批判上外党委怎样反工宣队。他们的揭发出什么呢?不外是党委书记要工农兵学员考试,称这是“违反了政策的”,就是不要考试。挑动起一部分不赞成考试的工农兵学员批判学校党委,说这是给工农兵学员“出难题”,校园里又贴出了许多大字报。第二个例子是下乡劳动还要不要学外语,搞不搞晨读,我作为校党委书记力主学生下乡劳动也要上课、学外语、也要搞晨读。
我在下乡的时候,发现有一部分老师顶住压力给学生上课,我给予肯定和支持,这也成了反工宣队的“罪证”。但这两个例子揭发出来后没有什么人响应。批判会开了好几个开不下去了。大部分老师、学生就是不肯发言,光是几个工宣队员在嚷嚷。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搞不下去了。后来市革委会里派的工作组就悄悄地跑掉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王秀珍押到上外开她的批判会。在大会上,责问她为什么说上外党委反工宣队,她支支吾吾地讲不出个所以然。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位上外78届的工农兵学员,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他以后调到了北京新华社工作。应该说他在校期间学习西班牙语还是学得不错的。然而他当时反对考试也是很“积极”的。1979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来党校找我,向我赔礼道歉,说他当时受了工宣队的影响。还有当时上外英语系四班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也贴得很起劲。后来有一位同学,是干部子弟,他是班长,也特地来向我赔礼道歉。这些工农兵学员还很年轻,能够认识到当时的错误,主动来向我赔礼道歉,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谓“党委书记反工宣队”,这可是当年上外发生的很大一个事件呵。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上海市委组成,那时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来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以苏倪彭为主要领导的市委经过半年时间的考察和核实,对上外党委重新作了任命,任命我仍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已是彭冲同志在上海主政,苏、倪都回了北京。
3.拨乱反正,上外恢复元气逐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上外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怎样开始的呢?当时首先要把共产党员的思想解放出来,恢复学校的元气。要求党员带头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把这作为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那时主要从党内开始动员揭批“四人帮”,特别是对“四人帮”一伙在教育战线、文化战线的罪行进行揭批,整整进行了半年时间。我认为这是上外拨乱反正最为重要的一步。
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校党委及时组织师生员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罪行及造成的恶果,正本清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然这期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曲折,那就是“两个凡是”对否定文革以及以往“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干扰。“两个凡是”不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就不能从根本上搞清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1977年邓小平同志的再次复出,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同志的批评,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实现得了的。所以思想解放,把党员、党组织的元气恢复过来,当时也不是能一气呵成的。
这里还涉及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党内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文革对党员思想的禁锢、约束并不是随着文革的结束而一下子就能改变的。
为什么当时首先要从党内开始揭批“四人帮”,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那时校党委主要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同时以实际行动迅速和毫不犹豫地根据中央、市委的指示,平反建国后和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我对中央关于迅速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从心底拥护,所以在上外,我是坚定不移、不遗余力地执行和落实这一得民心、顺民意的政策。
在“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上外干部、教师遭到立案审查的有300人,其中被公安局拘留的有14人,非正常死亡的有22人,被开除党籍、降级处分有2人。在原正副院长4人中,一人被打成“叛徒”,3人被打成“特务”。比如张培成同志,他是位资历很深的老同志,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过,后来去延安,当过毛泽东同志的翻译,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王明分子,关在监狱,关了十年多。还有王汝琪同志,她曾担任司法部法律司司长,后来担任上外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还兼任附中校长。这位老同志过去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东北、北平的地下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王季愚同志、张子钦同志,他们都是老党员、老革命、“老延安”,文革中都受到严重迫害。张子钦原任外贸学院副院长,他曾在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工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谭守贵同志,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西路军的连指导员,在西征时队伍被打散,他被马步芳的军队俘虏过,惨遭敌人毒打和强迫修公路,很受苦的,九死一生才回到延安,回到革命队伍。在文革中也被隔离审查,被打成“叛党分子”、“叛徒”。经过复查,这些同志平反昭雪,都恢复了名誉。与此同时,对历年来在各项运动中遭到错误处分的同志我们也进行了复查。
要想解决上外的问题,首先要抓住并解决上外原领导班子几位同志的问题,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和职务。我看了这么多老同志遭诬陷遭迫害的材料,心里很愤然很痛苦。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立了这么多功劳,最后竟惨遭迫害,搞得家破人亡。我认为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也好解决。校党委陆续为他们召开平反大会,恢复名誉,恢复职务。我作为校党委书记,坚决拥护中央、市委的决定。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中央、市委的决定,光是我个人也是解决不了的。
对于上外所谓“九类人”的问题,我们也费了半年时间,一个一个地看他们的材料,一一甄别平反。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上外被划为“右派”的有75人,其中处级干部1人,科级干部 3人,正副教授5人,讲师、教员5人,助教9人,学生52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复查,对包括全国著名的法语教授徐仲年在内的75名错划“右派”全都作了改正。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校师生,调动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大家真心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那时我还亲自带队,把曾遭受迫害、现已平反的同志组织出去旅游,让大家放松一下,做了一些安抚工作。
回想起来,我为有幸与上外广大师生员工一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参与了事关几百个人政治生命的工作而欣慰。更重要的是,平反上外大量冤假错案的这一段经历,使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建国以来,在极左路线的错误指引下,大搞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整人、压人所造成的损党害国害民的恶果是多么可怕!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灾难性危害和损失是多么巨大!这个教训是当前和今后的几代人都应该记取的!
4.探索高等外语教育改革,上外敢为人先作出了贡献
1978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了由邓小平同志提议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很受鼓舞。我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赞同小平同志说的“办学靠教师”的讲话。对此我深有同感。
我们上外学习和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大会,首先就是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抓教育、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指示。上外的老教师有教学的宝贵经验,是很值得我们推崇和学习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阶段,上外和其他高校一样,经历文革破坏,面临教师队伍的“青黄不接”。必须抓紧培养新的教师,要选拔青年干部、青年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我们留了一部分表现好、有培养潜力的工农兵学员,并有意识地选拔出学习成绩好的同志留校。还有那时“四年制外语培训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文革期间从上海各中学72届至74届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年轻,热情高,思想素质也不错。我们把这些培训班的班长和表现好的学生干部留了下来,作为学校今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培养对象。我认为这是当时上外党委做成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其作用和效应我们今天都能很清晰地看到。
1979年,上海市委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以后,上海市委和市教卫办作出了扩大招生这一重大决策。但因当时包括上外在内的各高校办学硬件设备严重不足,教师队伍也达不到扩招的需求,完成扩招任务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所以经过王一平、杨恺、舒文等市委及市科教办领导同志研究,为进一步发展上海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请示中央同意上海扩大招生。而为了扩大招生,就需要组成一个工作组,去香港采购教学设备。
当时由我、交大、外贸学院、市科教办一共5位同志组成了采购组,以我为组长,到香港去,为上海各高校扩大招生采购电化教学设备。这个报告让我带到了北京,向外交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当面作了汇报,请中央领导批准。
那个时候出国,去国外、境外采购,没有中央的批示可是不行的。我们的报告经过中央外事小组和耿飚同志(那时他负责中央外事工作)批准,中央领导同志都画了圈。我带上“批示”,组成了采购组去了香港,用了3个月的时间,采购了100万美金的教学设备。
我们上外成立分院也是在这么一个扩大招生的背景下搞起来的。那时上海各个大学基本上能办分校的都办起来了。没有那么多教师怎么办呢,只有靠电化教学。所以采购到的电化教育设备很快分配到各个高校去了。在这期间,我还拜访了国家外经贸委的同志、上海计委的马一新同志和市外办的同志,请他们给我们上外拨一点外汇,而我们则负担给上海外事部门培养外语人才。经国家外经贸委批准,给了我们5万美金,这5万美金我们都用在购买上外急需电化教学的主要设备上,其中包括把一部分购买的录音机分配给各位外语专业教师,那个时候录音机还是很稀罕的呵。
回顾这些往事,我觉得,我们上外确实为当年上海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和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作出贡献的。
还有一件事,是外语教学如何适应经济建设为现代化服务这一问题。当时校党委成员如胡孟浩等同志提出:办学要密切结合社会需要。面对当时各行各业都需要各类型外语人才的现实,上外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要着手搞多元化(复合型)。我也极力主张,把经贸系先搞起来是有条件的(因原外贸专业教师还在)因而党委一致决定:恢复经贸系。这对以后进一步组建新闻专业等复合型专业起到了探索作用,也拓展了上外办学的视角。
到1984年,我已经快60岁了,上级决定校党委书记由张显崇同志接任,我作为顾问。1984年我退下来了。建国以来我的工作经历尤其是在上外的那一段历史,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值得回顾总结的,也作为我在今天依然老有所为、继续发挥余热的一个动力吧。
5.回忆与思考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有某些地方的失误也是难免的。比如说,在教育方面,曾经有人说教育要产业化,结果很多学校普遍实行收费。在社会上造成了贫寒子弟上不起大学的现象。这个要总结经验教训。
另外对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之前和以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我思想上是有抵触甚至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也要靠搞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来促进各项工作,这是典型的极左路线。可以说,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是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上外各项工作的开展中,我没有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在拨乱反正中我也没有搞群众运动去整人。所以,文革后上外没有再出现一个冤假错案。在清查所谓“三种人”的过程中,我也没搞群众运动,因为我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恶果看得很清楚,教训极为深刻啊!
彭冲离开上海后,中央派来了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任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当时正在搞清查“四人帮”余党的工作,我对派工作组搞群众运动这一套“传统做法”是反感的。因为文革这笔帐主要不能让干部、教师负责。那是上面发动的。主要责任在上面。特别是在教育这条线上,在中学和大学风行一时的所谓“红卫兵运动”,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文革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下面的广大师生尤其是青年学生是“忠于毛主席”,响应号召“奉旨造反”的。应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其中很多人对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是后悔莫及和加以反省的。所以我对清查运动不太起劲。
文革期间,主要在1968年至1970年期间,全国各地搞过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在工宣队指使下,上外有一些干部群众参加了一些“内调外查”。现在你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有点讲不过去。所以,一些参与过此类事情的同志,只要他们认识到错误就可以了。在上外的清查工作中,我们一次群众运动也没有搞,也没有发动师生“揭发”。对派来的一些“调查组”的做法,我是有抵触情绪的。
对当时党内的学习教育特别是老同志的学习教育,我主张首先是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实现解放生产力,才能把人的干劲鼓起来。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和“左”的一套做法。虽然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还不能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我实际上做了这样的打算,即使我当不了党委书记了,也决不去搞“左”的那一套。
我们当时校党委有个别同志对我坚持清查工作不发动群众、不搞群众运动的主张很不满意。以后市教卫办让我和他去专门汇报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情况。我汇报以后,市教卫办的领导同志问我:“您看上外是否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说:“是的,清查工作可以结束了。”市教卫办的同志说:“好,同意你的意见。”这样,校党委那位同志也就不吭声了。所以,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市委领导的正确,上级领导不断改进工作做法的话,我一个人也是很难改变局面的。我当时的想法是,情愿我不干了,也决再不搞“左”的一套。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党的十七大召开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在全国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等,我是从心底里高兴和拥护的。我们国家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问题是,中央的政策要落实到下面,就要靠下面干部的实际水平和党性素养来体现。现在一些如“三聚氰胺”一类丢人的事,都是下面干部不执行中央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所以,我认为,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真正领会。我们自己一定要闯出自己的路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没有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的。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最近闹金融危机,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要搞自己的。总而言之,坚决不能搞过去极“左”的一套了。
几点看法和建议
趁此机会,我对我校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谈些看法。
我认为,30年来的历届校党委一直是始终紧跟党中央和听从教育部、上海市委领导的。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上外更是取得了飞跃般的发展成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要在新的起点上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30年来,上外改革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面临的新挑战。要在新的起点上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凝聚全校党员、教师的力量,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创建一流大学而奋斗。必须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继续努力奋斗。要以校第十二届党代会上和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提出的“四三二一”发展战略为目标,继续制定和完善具体的实施规划。要鼓舞起师生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坚定信心。
二、注意处理好几对关系:
1.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外既要以教好学好外国语为本,又要注意培育新的专业和特色。这其中就要注意语言类专业和非语言类专业之间的合理发展和资源配置;还应注意和其他同类或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促成共同发展。
2.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传统上外办学的基础,也是保证上外持续发展的前提。所以,要重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各专业的经验。创新是上外发展的动力,要保持上外的科学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蓬勃生机,就要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这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上外近年来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引领和服务社会的关系:这对关系在上外发展过程中是逐步实现和不断提升的。适应社会需求,引领社会和服务社会是包括上外在内的所有高校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不仅在教学上要有所表现,在管理资源、后勤服务等方面服务社会方面也要有新的作为。此外,随着离休干部进入“双高期”和退休人员的逐年增多,要继续重视上外离退休工作,支持校内外各类老年事业的发展。
4.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国际化是现代化大学的重要指标,只有加强和世界各国优质大学的交流、合作,才能拓宽师生的视野,提高办学水平,扩大上外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上外党政领导做了不少工作。校党委一再强调,要把上外建成高水平多科性国际化的研究教学型大学,并已初见成效。当然还要继续努力。本土化是指立足我国实际和民族传统特点以及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与水平,在此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世界优质大学的先进经验。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消化吸取再创造。目前,很需要在校各级领导中、教师队伍中总结办学经验与办学实践,推动再发展。
5.上外党政各级领导同志与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工会、团委等)尤其是与离退休老同志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办好上外、使上外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我个人观察,现在这方面的关系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大进步。其中对老同志们的工作中的重要一条是:要吸取他们在各个时期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各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最后,我对这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视角卫党委党史办公室“抢救与征集老同志党史资料”的工作表示由衷感谢。我认为,“抢救与征集老同志党史资料”很有必要。我被列入市科教系统的“抢救和征集名单”,这体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对我本人的关怀和对上外党史工作的重视。同时,这也是党对我本人一次很好的教育和激励。我要永远保持革命精神,保持天天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好习惯。老同志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清晰的判断能力,才有可能继续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否则,已相继进入“双高期”的离休老同志,不知哪一天到马克思那儿报到,而未能在健在时就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等作为“党史资料”保存下来,那就对不起党组织,也对不起后人了。
(采访、整理人缪迅:上海外国语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电话:13818282630;021-65311900-2402,联系地址:200083,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