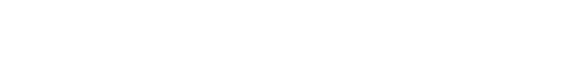1955年,我考入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外前身),从此开始和上外长达50多年的不了情。在上外,我开启了人生美妙的新篇章;在上外,我尽情享受了博大精深的中外文化内涵;在上外,我结识了毕业于二医、在上外附中医务室工作与我相伴终生的老伴。更巧的是,我女儿、女婿都毕业于上外,我的儿子也毕业于上外附中初中部,我的外孙女去年考入了上外英语学院国际公务员班。上外已经成为我家三代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会考上外?这有其偶然性。1955年我因海外关系原因离开部队后,决心报考大学。考理科还是考文科?我为此而徘徊不定。由于我是从海外归来的,数理化程度很差。所以压根就不敢碰理科。同时考虑到我是海外归侨,加上在福州三一中学教会学校念过高中,英语基础相对较好,便决定报考英语专业。当时,我只看重北京和上海两地。于是我报了北外、北大英语专业;报上海的原因是因为我姑妈在瑞金医院小儿科工作,而上海俄专当时还没有英语专业,只好报了俄语。在报考上外之前,我见到过上外很精美的校况介绍。其中有学生陪着苏联专家到处出访。这很让我为之着迷。
入学不久,适逢苏联大马戏团访问上海。我当时是班上团支书,就与班上几个同学商量写了一封热情的邀请信,邀请苏联大马戏团来校演出,他们居然真的来了。我们当时也不懂得什么是外事纪律,没有经过学校的同意就冒冒失失地发出邀请。学校也一下子懵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在上外我有欢乐,也有辛酸。最初几年,学俄语是非常吃香的,经常到机场接外宾,我记得有一次去机场迎接的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亲王头一回到中国,那时他可是很年轻啊。在上外,我们每周末都有舞会。我是调干生,每月发30多元费用,比起其他同学来,生活是非常惬意的。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搞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就连绵不断。什么“树红旗,拔白旗”,加上中苏交恶,俄语被打入冷宫。我们年级的许多同学都转了专业,有的改学英语,有的改学法语、有的改学德语。可是我却没有转专业,一直坚持到1959年毕业留校。
我毕业留校不久,因洛阳某新建高校缺乏师资把我派去顶替,我是部队下来的,颇有服从组织安排的自觉性,便义无反顾地走上新的岗位。十几年过去后,我从洛阳调回了母校上外。这时许多人不认识我,以为我是从外校调来的。
重返母校后,我起初在英语系工作,在那里我和许多老师结下深厚友情。语音学家许天福教授与我是福建同乡,他经常邀我到他家玩。杨小石教授现在已年近九旬,我们关系也很好。章振邦教授、林晓帆教授都是英语界权威,当年我们在一起工作,现在也在同一个离休支部。
后来,我改行搞电教,负责主编国家核心刊物《外语电化教学》,苏州大学的顾佩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舒予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陈吉棠教授、同济大学梁淑妍教授等都是从在《外语电化教学》上发表论文开始走上他们的“学术之旅”的。
1991年我离休了。虽离开了岗位但依旧在发挥余热,起初在上外音像出版社,后来在上外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在外教社,我创造了利用电子邮件远程进行编辑的新纪录。旅美学者祁寿华的稿件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我这里修改之后,又退回去,朝发夕收,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作用。
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但我的心依然年轻。我天天在自己的博客上笔耕,在网上我交了许多朋友。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母校、为我们的祖国奉献一些微薄的力量。(施行,作者系我校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