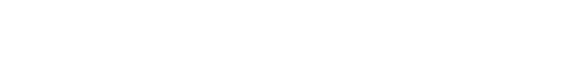1935年一个寻常的初秋下午,位于霞飞路87号的一家名叫圣克斯西餐厅的侍应生小杜正站在吧台擦洗一个高脚玻璃杯。这是上海一个宁静的秋日,一扇旋转门将西餐厅与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气儿切割成两个世界。西餐厅的留声机里播放的是小杜听不懂的西洋歌曲。暮色四合之际,有客人要求听周璇的歌的时候,小杜就将留声机的针起开,在里面搁置一张黑胶唱片。昔日甜美的歌声在整个西餐厅飘荡,听起来煞是哀婉。
这时,旋转门被推开。一个身穿蓝色天鹅绒旗袍,身段婀娜的女子出现在门口。她挎一只皮包,轻车熟路地走向临街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右手托腮,有几缕卷发生气勃勃却无不服帖地排在两颊。
魏婉兮坐定后,对着吧台一个长相清秀的服务员说:“给我一瓶最好的红酒。”她看见侍应生放下正擦拭着的酒杯去拿酒瓶后,就自己取出一根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漫不经心地吸起来。这是她最喜欢的女烟,不如雪茄烈。她吐出一个烟圈,有一点点烟雾萦绕在指间。今天她涂了豆蔻色的指甲油,十分好看。这样的豆蔻色让魏婉兮忽然想起一首杜牧的诗,题目她记不起来,只记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可惜她自己已经不是十三余,而是三十余了。今天,她来圣克斯餐厅等温老板。不过温老板是否会出现都还是个迷。
温老板是一个香港商人,他抽雪茄,烟斗大而华丽,当他拿着烟斗在唇边移动时,煞是神气。魏婉兮此时开始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温老板那天,自己还是个豆蔻梢头的女学生。穿一身素净的蓝色布裙,白色筒袜,黑色提兜鞋。站在热热闹闹的人群中心等电车。不时有黄包车贩殷勤地跑到她跟前,问道:“小姐,要不要坐黄包车?”魏婉兮通常都不睬这些黄包车夫,一会儿他们就自动悻悻地离开。这天,魏婉兮都等了超过3刻钟,电车都还没来,她正考虑要不要叫一个黄包车,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就停在了她的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温和的男人的脸,让魏婉兮想起一个十分宠爱自己的长辈。这个男人对她说:“学生,要不要我送你回家。”魏婉兮现在想起来那天竟跟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人上车简直是鬼使神差。或许是因为那天等了太久的电车,等得有些气急败坏;又或许是因为自己对小汽车内的所有谜感到好奇;再或者是自己足够年轻,承担得起所有可能的冲动的惩罚。就这样,魏婉兮开始熟悉小汽车内所有的秘密。
自然,这个人就是温老板。
小杜一面取酒一面观察着窗前的女子。年纪大概30出头。弯弯的眉毛精心修理过,一双眼睛虽然清澈却毫无生气,嘴唇的颜色和指甲的颜色一样鲜艳。声音有点沙哑,大概是烟酒过度的原因。一张脸生得十分艳丽。他想起自己中意的女学生,清汤挂面。脑海中心上人的脸和眼前女人的脸重叠在一起,小杜觉得头有些晕,遂摇了摇头。大概这就是人和人的不同吧。小杜暗忖。拔开软木塞,替客人斟好酒,就侍立一旁。女客人端起高脚杯,只啜一口,便又放下。小杜看到杯口留下一枚淡淡的唇印,似半朵凋零的玫瑰。
魏婉兮不爱喝红酒,但她享受喝酒的过程。特别是软木塞拔出来的那一瞬间,闻到那甘醇的酒香那一刻是她最愉快的时候。只消那一瞬,便可知这是一瓶好酒还是烈酒。如同看见人的眼睛一样,只消看一眼就晓得此人心术正直与否。不过她始终看不穿温老板的眼睛。尤其是当温老板带着魏婉兮穿梭于各式繁华酒会时,她觉得明晃晃的水晶吊灯下温老板亮晶晶的眼睛格外难以捉摸。她听着温老板一个个地跟她介绍周围的朋友。她统统不感兴趣。她只在乎温老板,只要能和温老板在一起,随便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自己可真够傻的。一颗心全吊在温老板身上,这是只有女孩才会做的事情。不过温老板也曾为自己也录过一张黑胶唱片。里面只有一首周璇的《天涯歌女》——“人生呀,谁呀不惜呀惜青春。”魏婉兮觉得自己的嗓子还是不错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特别识相的小弟告诉她:“魏姐唱得比周璇还好听。”
小杜看着客人啜了一口酒后就再也没有碰过酒杯。这时一个洋人走近女客人的桌旁,好像对着女客人说了些什么,女客人光是把玩手里的高脚玻璃杯,眼睛半笑着看着蓝眼睛的洋人。洋人站了一会儿就悻悻地离开了。
小杜觉得这就是在西餐厅工作的好处之一,每天可以遇见许多不可能奇异的事情。每天可以穿衬衫,打领结。回家后还可以擦皮鞋。还有和女伴聊天的谈资。小杜没有想过30岁过后自己会干什么。或许那个时候自己有一笔小小的钱。他可能会离开上海,回杭州,在靠近秦淮的地方开一家酒楼,中国风的酒楼。上海太过繁华,终究不适合普通人停伫。小杜不禁开始猜测起女客人的身份——少奶奶,不过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西餐厅?风尘女子,看妆容又不像。
魏婉兮开始回想她第一次和温老板的争吵。有一次,温存过后,魏婉兮躺在温老板胸口:“世杰,我给你生个孩子吧。”温老板戴着一副金框眼镜,正在翻阅当天的报纸,说:“好。”“那太棒了,你喜欢男孩,那我就给你生个男孩。”温老板说:“随便,反正我在香港已经有个儿子了。”魏婉兮不是不知道温老板在香港有家室,但是她从未问过另外一个她。她其实也有过好奇,但只是对陌生人的那种好奇,不是对
“不知道。”温老板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报纸。魏婉兮对这个答案有些吃惊,因为她以为,温老板出于敷衍也会毫不犹豫地选自己。然而他并没有,所以她女人的小性子就使了起来。“不行,不行,你今天必须选一个。”
温老板推了推金框眼镜,说:“大概还是她吧。”魏婉兮当下立刻怒不可遏,夺过温老板的报纸撕成好几份丢在床下。说:“凭什么选她不选我?”温老板大概也有些不快,说:“是你自己硬要我选的,现在怎么又随随便便生气。我跟他儿子都这么大了,不选他选谁!”
魏婉兮也怕彻底惹怒温老板,语气一软说:“我不也从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跟着你了吗?”
温老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那是你自愿的。”说着就气鼓鼓地下了床。魏婉兮呆呆地坐在柔软的钢丝床上,她忽然觉得温老板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皇帝,而自己就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失宠的妃子。她整理好自己的睡衣,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怜。但她同时又觉得温老板算得上个什么东西。很快她就回答了自己,温老板就是一张饭票,一个暂时可以下榻的旅馆。
不过魏婉兮就开始对自己的地位有了诸多不确定。
更让她觉得不安的是,自己的青春正在流逝。如果自己永远能够有18岁的热情,那该是多好的事。永远可以涂最艳的口红,永远可以开怀大笑。
小杜看了看店里的时钟,离下班时间还早。下班过后,小杜不能直接回家,他要去一趟医院。小杜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而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上星期最终住进医院。小杜每天必须去照顾她。小杜有一个女友,本来准备下个月底就结婚,这是小杜母亲托人算的黄道吉日。但是小杜母亲的病一发,整个事情就耽搁下来了。小杜甚至觉得假如自己母亲的病欠下一笔债的话,自己的女友会放弃和他结婚。
小杜有一段自己特别喜欢的时间,就是当他独个儿走回家的途中要经过的一条没有路灯的弄堂的时候。即使小杜慢慢走,整个弄堂也只花得了他4分钟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熟悉的漆黑中,他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安全感。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必看见。只是凭感觉在漆黑中前进,甚至都不必尝试探索。银河似乎触手可及。他感觉得到所有天文学家可以感受得到的宇宙。每一个人在宇宙面前都特别小。渺小,微小。
尽管第二天早晨起来经过的是同一条弄堂,但是小杜早晨经过他时只需最多1分半钟。一是因为弄堂口的豆浆油条晚几分钟就卖光;二是清晨的曙光将弄堂照得亮亮堂堂,没有夜晚的神秘感。曾有一次,小杜放慢脚步走过弄堂,却发现清晨的弄堂墙壁上贴的是各种广告、海报,广告上的女人涂一样的雪花膏。弄堂地上还有有不平的水洼,散着肮脏的烟头。从此以后,每天早晨经过这条弄堂的时候,小杜走得更快了。
魏婉兮看了一眼店里的时钟,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一刻钟前一个外国人问自己要点烟用的火柴。她抬头的时候从外国人胸前的怀表看见了自己的脸,一张东方的脸,于是她对着怀表上的自己笑了起来。外国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走出了西餐厅。她便再次陷入思索。她最近沉溺于走神。同时她发现走神让一个的思考变成思想。她一度沉溺其中,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在她一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她把所有发生过的都温习了一遍,把即将发生的都演习了一遍。她感觉宇宙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现在她眼睛开始扫描整个大堂。目光直落到身边的侍应生。他眉头微微锁,好像在思考其他的事情。皮鞋擦得光亮,想必有位娴熟的妻子。
罢了罢了,生活美满的年轻人。
她低头,再喝了一口苦酒。酒喝到底,等的人还没来。她决定离开这个餐厅,她记得
小杜帮女客人拉好桌子,女客人光是看了小杜一眼,说了句“珍惜所有的好天气,去笑吧。”小杜不明白为什么女客会莫名其妙地说出这句话,不过他也不以为然,每个醉酒后的人总是要说些奇奇怪怪的话的。他替女客推开旋转门。旋转门轻巧地转开,再次把他和女客切割在两个世界。他想起自己家的那扇老木门,每次推开它的时候,它是会发出“吱--嘎”的声音的。
(英语学院 萧敬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