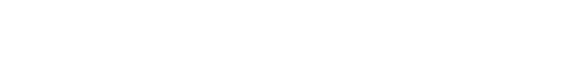文/井上的少年
一、
列车开始缓缓缓缓的加速向前,我在这一列离开的车厢里,轰鸣像是昨夜的哭声,四下是陌路人,路过的景色皆尽陌生。红皮列车擦肩而过的瞬间,车窗倒映的框画如同连帧的回忆,我听见心底某些东西破碎的声音,可我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呢,在无数的别离之前的夜晚哀号着离歌。
“我不能证明岁月有脚,但我确信它会奔跑。”一天一个月一年,我们把白天黑夜用二十四个小时分割,但即使一天只有十二个小时或是更少,依旧是在时间的渡河之中摇摆着前进,只不过嘀嗒不再是一秒钟。某个午后在那个海洋风的咖啡馆,喝着柠檬茶做着不愿离开的梦的时候,耳边是一些听也听不懂但听也听不厌的歌,时间就仿佛真的被按捺着走的慢了一些。墙上留着咖啡馆主人淡蓝色的一个梦,一扇紧闭着的蓝色的百叶窗,即使是用油漆简陋的画着,但那个梦在时间里,在空间里,在她千千万万个不愿醒来的午夜和清晨。可是一年之后呢,十年之后呢,岁月在无声无息的无情的奔跑着,你看到了吗,它带走了什么?
听到闹钟响起的那一秒,仿佛听到战争打响的号角,没有犹豫,也不能够犹豫,我只是恍惚间明白自己那个停留的梦像是缓缓上升的彩色气泡,我踮着脚够着企图触碰,可啪嗒一声,那个永恒的气泡从这个只有瞬间的世界消失了,去成全了另一个永恒。等到站台里响起机械般的女声,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企图告知,终点已经到达,可我心里漂泊的帆船,却迟迟没有能够靠岸。
“我们都习以为常地才能够此时此处回到家中,在我们的天气记载里我展示欢颜或忧愁。”可这座城市的天气,是否会变化无常的让我感觉到成人的新鲜,这座城市的雨天又是否能够一样打湿我的赧颜。我已经不能够再躺回母亲的子宫里,不能够以躲避祈求一份安宁。隔着很远,很远很远,我好像听到当初在母亲体内的时候那让人血脉喷张的脉搏声,一声一声,敲打着我思乡的灵魂。乡思,相思,当初是谁将一个字巧妙的改写,于是一处的思念在一瞬幻化成两处的怀念。远处的那片土地啊,是否也在那样月圆的夜,一次一次的在地表追寻着我的印记。
二、
烟迷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去到另外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来阐述心底所有的柔软和坚硬,棱角和平滑。就像五个字和五个单词,烟,迷你的眼。于是可以想象到袅袅的升烟,和一张烟雾里迷迷蒙蒙的没有边界的面孔,可他一定有明亮的眼眸。他们说这烟其实是精神鸦片,是爱情是那一段在时间里沉淀成一出悲剧的相恋,爱情就像烟,迷惑了谁的双眼。
可我又害怕,这座城市的繁华,会落人纸醉金迷的口实。烟迷,我的眼。
“即使命运先生一直觉得人类如此像一株蒲公英。”我被昨日的大风卷到另一座城市,没有准备开始,却不得不准备开始,我知道,人类在世事无常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并且不堪一击。那一座城市,有我过去全部的根植,我的笑和泪,所有言不由衷和情难自持。可那座城市,也注定了只能是拥有过去的城市,不是现在和将来。
“岁月啊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该得的得,该给的我给。”
三、
“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无比漫长/时间带着明显的恶意 /缓缓在我的头顶流逝/我咬紧牙关 /一直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暂落在这座城市,好像人人都自以为生命这一场飞行在蔚蓝天际的碧影之中能够无期限地进行,可电闪雷鸣,只需一刹那的暴风骤雨,谁又能够预料这架钢铁机器会被迫降在哪一个荒无人烟的草坪。
风大雨大。庞伟的建筑为人类的肉体遮蔽过一次又一次的风侵雨淋,只是钢筋水泥,永远也遮挡不住心里潮潮润润的雨季,就像那年的寒潮浸湿了基隆港的船舶,也让那个中年诗人的心苔衣遍地,听听这冷雨。可再听再听,也只有汽车呼啸的声音,像土狗趴在路面上重重地喘息。我总是幻想这是在英国的那座城市,所有的灰鸽扑闪的翅膀让早晨也灰蒙蒙像画家忧郁的眼睛,可是没有一声寒钟敲醒午后迟迟不肯回神的梦和魂灵。
四、
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那既不是重庆,也不是森林,只有熙攘的人群和被来往人流冲散的相遇。那年的阿菲还清清瘦瘦,那年的凤梨罐头上还印着黑色墨迹的日期,那年的每一通口讯都是传呼台小姐的嗓音,那一年的香港,也不过是一座石屎森林。迷迷离离的音乐和灯光,霓虹的喧嚣撕裂了黑夜阒静的表象,吧台和一杯伏加特,问一个陌生女子,你爱不爱吃凤梨,用粤语日语英语和国语。很多年以后,爱情的保质期变得比凤梨罐头还要短,又忽然会想起那个来自702室的生日快乐。如此种种,都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发生,可似乎时间并没有一台监控器,过去的影像都销声匿迹。我想这就是城市吧,而我现在也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只是我并没有听到心里的那头恶兽蠢蠢欲动的声音。
离她最近的时候我们的距离是0.01米,可六个小时之后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过是迷惑人的东西,谁告诉过我不要太过轻信。
五、
都说回忆如困兽。
六、
又想起大麦茶温温和和藏藏匿匿的淡淡香气,一圈一圈绕着旧日时光迟迟不肯散去。以梦为马的时光已经过去,想想那些日子,总以为自己的马驹豢养千年却依然食着牧场的苗圃,在界河边踱步啜饮,却迟迟越不过那条宽宽的河道。土地是幻梦的温床,采风为生的流浪者早就被时光遗弃,这个世界上唯物至上,形而上学的真谛也一直找不到答案。这里只有意式浓缩咖啡,要来一杯吗,长夜那么容易让人醉。
轮廓隐身在温柔的夜色里,在一座一座的高楼之间穿梭,有时候只是纯粹的压马路,一个人在路上走到很迟,偶尔遇到一个两个醉生梦死的年轻人,伏在绿化带边低低地哭,莫名想到韩寒的《我在上海,活得很好》。有些人功成名就,有些人摸爬打滚,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混不下去就滚蛋。只是我不知道,这跟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是否有一毛钱关联。我想也许是我水土不服。
那些,有伤的年轻人啊,我以为他们只生活在这样困住大雨的城市里。
七、
每一种罐头,都有自己的保质期,连保鲜袋,都有保质期。
我们的回忆,也有保质期吗?
有人爱在家里屯很多很多的沙丁鱼罐头,把它们堆叠成一座一座的城堡。可是那些沙丁鱼罐头,到了保质期,就会全部被送到废品站吗?
谁知道呢。
(东方语学院越南语系 胡银银)